村民诉镇政府《房屋拆迁协议》纠纷案的事实与法律之辩
前天 04:25
hzb691223
来自江苏
鹤鸣亭
2010年,射阳县原耦耕镇人民政府与当地村民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协议中明确承诺“由政府免费统一办理产权证”,然而,十余年间,村民不仅始终未能拿到协议约定的产权证,更在2025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意外得知当年的拆迁安置行为存在诸多违法情形:镇政府既无合法的拆迁审批文件,也未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发布拆迁公告、公示补偿安置方案,收回宅基地使用权时未履行“报原批准用地人民政府批准”的法定程序;安置地块实为农用地,直至2024年才补办相关手续,且村民所建的房屋也应违法用地在2023年就己被射阳县自然资源局没收,所谓“免费办证”的承诺,更是镇政府超越自身法定职权的无效约定。 得知真相后,村民以行政协议纠纷为由,将现合德镇政府诉至东台市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案涉《房屋拆迁协议》并判令镇政府赔偿损失。令人意外的是,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却以“超过民事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了村民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份判决最核心的不公,在于对证据的选择性采信——故意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程序违法、超越职权”等可撤销情形于不顾,仅在裁判文书中着重强调与《民法典》“欺诈行为”相关的内容,以此诱导公众聚焦“村民因欺诈签协议、房屋被没收”的表面事实,却对村民提交的、能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关键证据视而不见。 村民在诉讼中提交了多份直指行政行为违法的核心证据:射阳县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文件,可直接证实镇政府2010年实施拆迁时无合法审批手续;合德镇政府履责申请告知书,清晰印证“免费统一办证”的承诺超出镇政府法定职权范围。这些证据本可直接证明镇政府存在“未履行审批程序、未公示补偿方案”的程序违法,以及“超越职权承诺办证”的实体违法,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也是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关键依据。但一审在判决书中对这些证据避而不谈,只是强调政府以农用地置换宅基地安排村民建房,欺骗诱导村民签定协议,最终导致安置房被没收的违法事实刻意放大与“欺诈”相关的表述,以此为引用《民法典》除斥期间条款铺路,这种证据采信的倾向性,本质上是对案件核心争议的刻意回避。 更关键的是,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完全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明确,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也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可一审法院却绕开这些规定,未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知道或应当知道作为行政行为6个月内”和“不动产案件最长起诉期限20年”的条款,反而直接参照《民法典》中民事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规定,认定村民“撤销权已丧失”。 退一步讲,即便参照《民法典》关于欺诈行为的规定,镇政府的身份也并非普通民事主体——其代表的是政府公信力,村民当年签订协议,正是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对基层行政机关的信赖,从未想过代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签订存在违法欺诈内容的协议侵害群众权益。如今,因镇政府的违法承诺与程序瑕疵,村民即便现在仍居住在原房屋内,但从法理层面已失去对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合法财产权益陷入悬空状态。而一审法院却以“除斥期间已过”为由轻描淡写驳回诉请,完全忽视了行政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也未考量政府失信对公民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来看,一审判决更是未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明确,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超越职权”情形的,法院应判决撤销。本案中,镇政府未发布拆迁公告、未审批收回宅基地,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无办证职权却作出“免费办证”承诺,构成明显的超越职权。这些均是行政行为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也是村民诉讼主张的核心。但一审判决既未评价这些违法事实,也未回应村民的核心诉求,仅以“驳回诉讼请求”的实体判决回避审查,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驳回诉讼请求需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立法本意完全相悖。 行政诉讼的核心价值,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行政行为侵害。而本案的行政判决,却在证据采信上搞“双重标准”,刻意放大民事法律关系、回避行政行为违法的核心事实,在法律适用上避重就轻,在审查义务上选择性失明。这样的判决不仅无法让村民信服,更可能弱化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任。期待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能纠正一审的错误,全面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严格适用行政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还村民一个公正的裁判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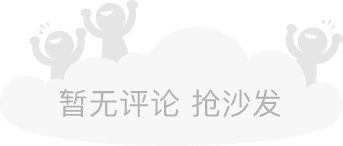
 游客
游客




